當(dāng)代歷史小說話語范式的轉(zhuǎn)型
所屬欄目:文學(xué)論文 發(fā)布日期:2019-06-12 11:24 熱度:
[摘 要] 1980年代中期以來,歷史小說掀起反叛元歷史話語的激進運動,當(dāng)代歷史小說話語范式發(fā)生了根本的轉(zhuǎn)型。這一轉(zhuǎn)型呈現(xiàn)出以下特征:由語言工具到語言本體;由歷史再現(xiàn)到自我指涉;由遵循語法到打破規(guī)范。歷史小說積極探索歷史話語運用的多種可能,力求提升歷史話語的審美價值,彰顯作家個體的話語風(fēng)格,元歷史話語被個人化歷史話語所取代。
[關(guān)鍵詞] 元歷史話語;個人化歷史話語;工具論;反映論;多元化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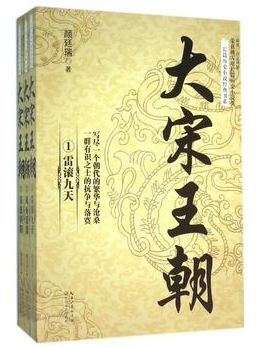
一、元歷史話語的生成
自 1942 年毛澤東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》發(fā)表以來,歷經(jīng)多次文藝整風(fēng)運動,當(dāng)代小說語言確立了政治話語霸權(quán)。受其影響,新中國成立以來至 1980 年代中期的歷史小說,如姚雪垠《李自成》、凌力《星星草》、徐興業(yè)《金甌缺》、巴人《莽秀才造反記》、任光椿《辛亥風(fēng)云錄》、顧汶光《大渡魂》、劉亞洲《陳勝》、楊書案《九月菊》等作品,局限于社會政治學(xué)范疇內(nèi),形成了政治化、工具化與理性化的元歷史話語體系。國家意識形態(tài)用先驗宏大歷史話語,如階級論、進步論與目的論,來規(guī)范不同個體表達歷史的大一統(tǒng)模式,從根本上取消了個體闡釋歷史的可能。從本質(zhì)上說,元歷史話語沒有擺脫中心論、決定論和有序論的特征:
第一,個人歷史話語的剔除。元歷史話語將意識形態(tài)滲透到字里行間,實現(xiàn)現(xiàn)實秩序合法性論證。創(chuàng)作個體被剝奪闡釋歷史的話語權(quán),只有無條件融入人民創(chuàng)造歷史的元歷史話語之中,上升為階級代言人才具備合法性,從而剔除了個人歷史話語生成的可能。如任光椿《辛亥風(fēng)云錄》:“我的心情同你們的心情也是一樣的。我黃興也絕不會辜負你們和成千上萬的盟友同志、愛國僑胞和全國民眾的期望。但是,我們必須有紀律,任何個人都不應(yīng)該隨意動作。”[1](p245) 再如巴人《莽秀才造反記》:“然而,太平天國反對的統(tǒng)治者,正是前一朝代的統(tǒng)治者引入的異族;而這回天字第一號的漢奸曾國藩、李鴻章,卻為他舊日的統(tǒng)治異族,一再引入新來的眾多異族;豺狼戰(zhàn)勝不了中國的人民,卻又放入獅虎來嚙咬中國人民的骨肉了!”[2](p5) 上述兩段引文文本充斥著“人民”“同志”“國家”“起義”等宏大歷史語匯,作家個體語言風(fēng)格消失殆盡。
第二,語言再現(xiàn)歷史的反映論。元歷史話語存在根深蒂固的反映論,認為歷史小說語言能像鏡子一樣映照出曾經(jīng)發(fā)生過的歷史事件。小說語言與真實歷史互為鏡像,從而為意識形態(tài)提供歷史論證。為了實現(xiàn)宣傳教育目的,只有確保歷史語言的真實性,才能使人們信服歷史本質(zhì)的存在,否則不具備說服力。因而元歷史話語對歷史人物、事件甚至細節(jié)都要還原歷史,嚴格遵循史料考證。比如姚雪垠的《李自成》,“就連諸如銀子和制錢的比價變化、黃錢和皮錢的關(guān)系,崇禎案頭放些什么器物、北京戒嚴應(yīng)由哪個衙門出布告等也務(wù)求精細”[3](p105) 。顧汶光《天國恨》中的人物甚至連細節(jié)都與史書記載完全一致,盧賢拔兩耳重聽、向榮瘦小瘸腿等都有據(jù)可查,徐興業(yè)《金甌缺》中劉锜、馬擴每一次職務(wù)調(diào)動,參加的每一次戰(zhàn)斗,都與史實完全吻合。拘泥于歷史的創(chuàng)作原則禁錮了作家的藝術(shù)創(chuàng)造力,導(dǎo)致當(dāng)代歷史小說語言史重于文的缺失,淪為正史的通俗教科書。
第三,嚴格遵循語法規(guī)范。為了宣傳政策路線思想方針,意識形態(tài)要求歷史小說語言必須通俗易懂,句式力求簡單準確,讓文化水準不高大眾能看懂,以實現(xiàn)最大覆蓋范圍與最佳宣傳效果。比如劉亞洲《陳勝》:“他把手一揮,用洪亮的聲音喊道:‘弟兄們!大家不要慌亂!’這一招真管用,人們立即恢復(fù)了剛才那種安靜。”[4](p235) 顧汶光《天國恨》:“三娘猛然一聳肩,后退了兩步,再一次仔細地打量兒子。短短的一瞬間,她的淚水干了,她的笑容消失了。三娘緊張地思索著。”[5](p801) 閱讀那個時代的歷史小說,我們就會發(fā)現(xiàn)小說語言嚴守語法規(guī)范,不但在修辭上刻板單調(diào),而且在句式運用上也缺乏變化,繁復(fù)多變的文學(xué)句式被簡化為單一的公文句式,削弱了歷史小說語言的藝術(shù)表現(xiàn)力。這典型折射出文學(xué)體制對歷史語言的嚴格控制,為了實現(xiàn)意識形態(tài)宣傳目的,小說語言準確無誤的傳達功能被強調(diào),呈現(xiàn)出理性化、實用化與透明化特征,而文學(xué)語言自身的審美性則被窒息。從根本上說,十七年乃至“文革”時期的工具論語言觀是其根源所在。
第四,語匯的高度政治化。語匯是構(gòu)成語言的基本單位,包括語素、詞語和短語,不僅直接決定語言的風(fēng)格特征,而且受到特定時代背景、文化語境、意識形態(tài)等諸多因素制約。歷史小說作家受到革命歷史理論影響,小說語言充斥著大量政治語匯。比如顧汶光《大渡魂》:“首領(lǐng)們都在大營里議事。娘子軍根據(jù)馮云山的指示,開赴新的戰(zhàn)場去了。” “失敗也是暫時的,腐朽的清朝政權(quán),必定會被后來者推翻。”[6](p262) 此外,歷史小說語言經(jīng)常出現(xiàn)具有鮮明政治隱喻色彩的詞語,比如“紅日”“朝霞”“紅旗” “黑暗”等,如顧汶光《天國恨》:“對,應(yīng)該是這樣的!洪秀全指著噴薄的紅日,豪邁地一笑:我們的天國,百姓的天國應(yīng)該是這樣的!”[5](p829) 歷史小說語匯嚴格限制在社會政治范疇內(nèi),政治教育與軍事斗爭語匯充斥于歷史小說文本之中,歷史文化、日常生活、情感心理的語匯近乎空白,因而形成了封閉的詞匯體系,顯得呆板凝滯,缺乏藝術(shù)表現(xiàn)力。
第五,鮮明的價值判斷。元歷史話語具有價值判斷與情感色彩截然對立的兩套話語體系。在描述進步歷史人物形象時,無論是語匯還是敘事語調(diào)都與美好、光明、高尚聯(lián)系在一起,表明作家對其主流意識形態(tài)價值取向的遵從。比如凌力《星星草》: “朝霞披在張宗禹的身上。他挺拔魁偉的身材,緊稱合身的藍色戰(zhàn)袍,頎長寬大的黑色披風(fēng),顯露出慷慨瀟灑的風(fēng)度。臉上兩道劍眉直射鬢邊,雙目奕奕有神,襯著端正高直的鼻準,棱角分明的嘴唇,就在面臨著捻軍可能覆滅的時刻,也沒有絲毫改變。”[7](p31) 作家把盡量多的褒義詞語用在正面人物身上,隱含著政治價值判斷標準,即便是“朝霞”“紅旗”“旭日”也失去了其所指的原初意義,作者并不是進行客觀景物描寫,而是承載著烘托歷史人物革命信念的功能,蘊含著深刻的政治意義。對于反動歷史人物,元歷史話語則選取另一套話語體系,如巴人《莽秀才造反記》:“朱神父慢慢抬起了頭,肥胖的袋形的臉子,漸漸消逝了惘然的情調(diào):他漸漸把一種力量,集中到他一對眼睛上去。他那浮腫的眼皮長上了一對滾圓的前突的眼珠子,火龍似的吐出光來,直盯著眼前那女人。”[8](p97) 作者運用貶斥性話語對朱神父形象進行丑化,除了肥胖的臉與浮腫的眼皮之外,讀者無法讀到關(guān)于朱神父的任何人性描寫,暴露出類別化、概念化與臉譜化的藝術(shù)弊端。作者并不是以刻畫藝術(shù)形象為目的,而是通過對反面人物形象的丑化,旨在表明愛憎分明的政治立場。
從上述五個特點看出,元歷史話語把語言視為工具、手段與載體,還停留在實用語言的層面上,作家僅僅關(guān)注語言的表意功能,審美功能則被忽視,因而歷史小說語言的文學(xué)性大大地弱化了,而為政治服務(wù)的工具性卻不斷被強化。因而作家的語言觀念長期處在工具論的陰影下,從根本上導(dǎo)致了歷史小說語言的單一與滯后。
二、工具論語言觀的破除
1980 年代中期以來,隨著意識形態(tài)禁錮的松弛以及西方語言本體論思潮的涌入,當(dāng)代小說語言觀念發(fā)生重大變革,工具論語言觀逐漸被本體論語言觀所取代,回歸語言自身已經(jīng)成為文學(xué)界的共識,俄國形式主義認為文學(xué)語言與實用語言的區(qū)別在于:“經(jīng)過陌生化處理的文學(xué)語言,不負載一般語言的意義,喪失了語言的社會功能,而只有‘詩學(xué)功能’。如果說,日常語言具有能指(聲音排列組合的意義)和所指功能(符號意義),那么文學(xué)語言只有能指功能。”[9](p47) 小說語言問題成為文學(xué)理論熱點問題,受到了評論界前所未有的重視,1985年黃子平《得意莫忘言》提出本體論的語言觀,“文學(xué)作品以其獨特的語言結(jié)構(gòu)提醒我們:它自身的價值。不要到語言的后面去尋找本來就存在于語言之中的線索。”[10](p86-90) 1986 年汪曾祺《關(guān)于小說語言》認為寫小說就是寫語言,小說語言和小說內(nèi)容是融為一體的,語言是小說的載體同時也是小說的目的等 [11](p57-60)。1988 年《文學(xué)評論》發(fā)表程文超、王一川、陳曉明等人筆談《語言問題與文學(xué)研究的拓展》。以上探討促進了小說語言觀念的變革,將小說語言從工具論的桎梏中解放出來,對歷史小說作家語言觀念轉(zhuǎn)變起到推波助瀾作用,莫言認為:“我想一個有追求的作家,最大的追求就是語言的或曰文體的追求,總是想發(fā)出與別人不一樣的聲音或者不太一樣的聲音。”[12](p115) 格非指出:“新的形式、文體、語言、技巧、變革是文學(xué)的生命。當(dāng)作家的筆拿起來時,寫作就沒有任何陳規(guī)陋習(xí)的限制,對現(xiàn)實本身我在寫作時首先考慮的是語言文體。
三、歷史反映論的顛覆
由于歷史小說題材的特殊性,小說語言除了具備普范性文學(xué)語言特征,更要受到歷史的規(guī)約。正是在這一點上,以海登·懷特、安克·施密特、羅蘭· 巴特為代表的西方后現(xiàn)代歷史哲學(xué)思潮,通過揭示歷史語言的意識形態(tài)性和非透明性,戳破了如實再現(xiàn)歷史真實的神話。羅蘭·巴特認為,不存在歷史事實本身,而一旦語言介入,事實就不可能是歷史真實的復(fù)制品了,必然糅雜著闡釋者的主觀判斷和價值取向,檢驗歷史的試金石與其說是現(xiàn)實,不如說是可理解性。海登·懷特指出,歷史從本質(zhì)上說是語言的存在,“話語被看作是一種生產(chǎn)意義的手段,而不僅僅是一種傳遞有關(guān)外部指涉信息的工具。”[15](p34) 后現(xiàn)代歷史哲學(xué)站在語言本體論的立場上,通過分析歷史語言的文本性、修辭性與敘事性,解構(gòu)了占據(jù)統(tǒng)治地位的歷史反映論,“在可理解的意義上,一切歷史事實都依賴于它如何被敘述。對于人們來說,發(fā)生在另一個時空體系的事實,是通過語言的敘述才進入我們的視野的。”[16](p232) 歷史語言與歷史事實完全契合的反映論被解構(gòu),歷史小說語言從再現(xiàn)歷史的禁錮下解放出來,回歸到文學(xué)語言自身。受到西方后現(xiàn)代歷史哲學(xué)思潮影響,歷史小說作家顛覆了如實再現(xiàn)歷史的信條,不再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來組織語言,而是擺脫了對歷史亦步亦趨的依附,從根本上將語言與歷史客體隔離開來,通過無拘無束的主觀虛構(gòu),建立起自我指涉的語言王國,真正做到了西方語言哲學(xué)所倡導(dǎo)的“文本之外無他物”。這突出體現(xiàn)在1980 年代后期勃興的新歷史小說,小說語言既沒有具體的歷史背景,也沒有真實的歷史人物,讀者得不到關(guān)于真實歷史的信息。作者津津樂道于人性的丑惡與生存的困境,描繪出陰暗恐怖的灰色生存圖景,具有濃重的寓言化與哲理化特征。
四、歷史話語規(guī)范的突破
新中國成立以來,元歷史話語嚴格遵循語法規(guī)范,淪為意識形態(tài)宣傳的載體。茅盾指出,作家對語言規(guī)范的遵守事關(guān)能否準確傳達黨的方針政策, “我們應(yīng)當(dāng)把學(xué)習(xí)普通話,今后是學(xué)習(xí)漢語規(guī)范化,看作不但是提高寫作能力的必要的措施,而且是一項政治任務(wù)。”[23](p161) 隨著歷史小說話語范式的全面轉(zhuǎn)型,歷史小說作家以決絕而激進的方式顛覆歷史話語規(guī)范,拆解強加在歷史小說語言上的種種禁錮,對歷史語言進行變異以實現(xiàn)陌生化的藝術(shù)效果,以凸顯歷史話語自身的審美價值。
第一,語匯。當(dāng)代歷史小說語言的語匯由于受到意識形態(tài)的限制,主要局限于社會政治學(xué)領(lǐng)域, “革命”“階級”“封建”成為出現(xiàn)頻率最高的語匯,而其他領(lǐng)域的語匯諸如情愛、人性乃至潛意識都被列為禁區(qū)。轉(zhuǎn)型后的歷史小說語言則打破了政治語匯的單一與狹隘,顯示出前所未有的開放性與兼容性,各個領(lǐng)域的語匯都匯集到歷史話語中,特別是以往被視作禁忌的丑惡的、病態(tài)的乃至骯臟的語匯也堂而皇之具備了文學(xué)語言的資格,體現(xiàn)出歷史小說語匯的多元與駁雜。除了語匯覆蓋面的急遽擴充,歷史小說語言還通過對常規(guī)語匯的變異、重組與反常使用,從而產(chǎn)生了陌生化的藝術(shù)效果。
(1)她像對待不聽話的小男孩一樣,生吞活剝了他的衣裳(莫言《豐乳肥臀》)。(2)枯黃的樹葉和草尖上覆蓋了一層薄霜,鳥兒遲暮地飛走了(格非《青黃》)。(3)王公貴族們肥胖的身影形同鬼魅,峨冠博帶與裙釵香鬢一齊散發(fā)著盲目的歡樂氣息(蘇童《我的帝王生涯》)。(4)神圣的太宗皇帝在媚娘心目中已經(jīng)淪為凡夫俗子,從此她常常在天子之軀上聞到一股平庸的汗味(蘇童《武則天》)。上述的例句都屬于語匯的反常規(guī)使用,語匯在日常語境中都有著約定俗成的含義與用法,而歷史小說語言卻打破語匯的正常使用規(guī)范,或是改變詞類的屬性和意義,或是故意打破詞匯的固定搭配,力圖通過詞語變形使得語匯產(chǎn)生陌生化的藝術(shù)效果,使讀者產(chǎn)生新奇的閱讀感受。
比如(1)句中的 “生吞活剝”在日常的交流語境中,較多與思想文化搭配,很少作為動賓短語使用,而這個句子卻反常規(guī)地與“衣裳”搭配構(gòu)成動賓結(jié)構(gòu),違背了常規(guī)的詞語使用規(guī)范,呈現(xiàn)出新奇另類的語言風(fēng)格。(2)句中的“遲暮”一般作為形容詞使用,而在句子中卻臨時改變了詞類的屬性,被轉(zhuǎn)換為副詞使用。(3)(4)句中的“盲目”與“平庸”作為定語來修飾名詞,形成了固定的用語規(guī)范,不能與“氣息”與“汗味”搭配,而上述句子中則違背了語言邏輯,強行將其搭配在一 起,對常規(guī)語匯進行變形,從而使得語匯臨時改變固定的含義與語法功能,傳達出正常語境下難以表達的藝術(shù)效果。
第二,修辭。作家為了加強語言的藝術(shù)表現(xiàn)力需要運用修辭技巧 ,當(dāng)代歷史小說語言由于受到工具論語言觀的束縛,僅僅局限于常用的比喻、擬人和象征。轉(zhuǎn)型后的歷史小說語言廣泛運用諸多的修辭手段,除了比喻、擬人等常用修辭,還綜合借鑒通感、反諷、回環(huán)、反復(fù)、戲擬等修辭,增強語言的藝術(shù)表現(xiàn)力。即便就單一的修辭方式而言,作家也竭力打破常規(guī),力圖創(chuàng)造新穎的修辭效果。以常見的比喻修辭為例,元歷史話語中的比喻修辭較多為明喻,本體與喻體之間的相似點較多,形成了固定化的比喻模式,如果本體是正面人物或事物,喻體多為青松、朝霞、紅日、黎明、拂曉等光明意象,對于反面人物則有著另一套截然相反的比喻修辭模式,從而使歷史語言具有鮮明的政治敘事特征。轉(zhuǎn)型后的歷史小說修辭拉開本體與喻體的距離,弱化二者之間的相似度,喻體擺脫了對本體的依附。
第三,語法。當(dāng)代歷史小說的語言為了準確無誤地傳達意義,語句必須嚴格遵守語法規(guī)范,不僅作為句子成分的主語、謂語、賓語不能無故缺失,而且彼此之間的搭配必須嚴守約定俗成的語法規(guī)律制約,語句表意力求完整、準確與直白,具有鮮明的新聞報道式的工具語言特征。隨著歷史小說語言向本體的回歸,作家試圖打破語法規(guī)范,通過對句子成分的省略、扭結(jié)與反常搭配,對歷史小說語言進行變異,增強歷史小說語言的藝術(shù)表現(xiàn)力。
五、結(jié)語
1980 年代中期以來,歷史小說創(chuàng)作掀起了反叛元歷史話語的激進運動,當(dāng)代歷史小說語言范式發(fā)生了根本的轉(zhuǎn)型。這一轉(zhuǎn)型呈現(xiàn)出以下特征:一是由語言工具到語言本體。元歷史話語為了準確傳達方針政策,要求語言必須準確明白,價值判斷鮮明,不允許有絲毫的歧義與模糊,淪為簡單的傳達意義的工具。轉(zhuǎn)型后的歷史小說語言回歸文學(xué)語言本體,具有豐厚的象征與隱喻的含義,賦予讀者廣闊的藝術(shù)想象空間。二是由歷史再現(xiàn)到自我指涉。元歷史話語的信條是通過歷史話語真實再現(xiàn)歷史,轉(zhuǎn)型后的歷史小說語言則顛覆了這一基本原則,其語言符號與歷史本來面目剝離,僅僅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,營造出僅存在于語言自身的意義空間。三是由遵循語法到打破規(guī)范。元歷史話語嚴格遵循語法規(guī)范,顯得呆滯拘謹缺乏活力。轉(zhuǎn)型后的歷史小說語言則以其敏銳的藝術(shù)感悟力,大膽反叛日常語言規(guī)范,積極探索歷史話語運用的各種可能,提高了歷史小說語言的技術(shù)含量。1990 年代隨著我國政治、經(jīng)濟與文化體制的全面轉(zhuǎn)型,元歷史話語最終被個人歷史話語所取代,不同個體依據(jù)不同審美觀展開自由的話語言說,先鋒話語、民間話語、女性話語、網(wǎng)絡(luò)話語等,從元歷史話語破裂處噴涌而出,歷史小說語言變得前所未有瑣碎與多元。
參考文獻:
[1]任光椿. 辛亥風(fēng)云錄[M]. 長沙:湖南人民出版社,1983.
[2]巴人. 莽秀才造反記[M]. 北京:人民文學(xué)出版社,1984.
[3]吳秀明. 在歷史與小說之間[M]. 長春:時代文藝出版社,1987.
當(dāng)代歷史小說話語范式的轉(zhuǎn)型相關(guān)論文期刊你還可以了解:《再論歷史研究的范式轉(zhuǎn)型 ——當(dāng)代西方史學(xué)若干前沿問題》
文章標題:當(dāng)代歷史小說話語范式的轉(zhuǎn)型
轉(zhuǎn)載請注明來自:http://m.anghan.cn/fblw/wenyi/wenxue/40309.html
相關(guān)問題解答
攝影藝術(shù)領(lǐng)域AHCI期刊推薦《Phot...關(guān)注:105
Nature旗下多學(xué)科子刊Nature Com...關(guān)注:152
中小學(xué)教師值得了解,這些教育學(xué)...關(guān)注:47
2025年寫管理學(xué)論文可以用的19個...關(guān)注:192
測繪領(lǐng)域科技核心期刊選擇 輕松拿...關(guān)注:64
及時開論文檢索證明很重要關(guān)注:52
中國水產(chǎn)科學(xué)期刊是核心期刊嗎關(guān)注:54
國際出書需要了解的問題解答關(guān)注:58
合著出書能否評職稱?關(guān)注:48
電信學(xué)有哪些可投稿的SCI期刊,值...關(guān)注:66
通信工程行業(yè)論文選題關(guān)注:73
SCIE、ESCI、SSCI和AHCI期刊目錄...關(guān)注:120
評職稱發(fā)論文好還是出書好關(guān)注:68
復(fù)印報刊資料重要轉(zhuǎn)載來源期刊(...關(guān)注:51
英文期刊審稿常見的論文狀態(tài)及其...關(guān)注:69
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期刊評估...關(guān)注:58
文史藝術(shù)論文范文
播音與主持論文 動畫藝術(shù)設(shè)計論文 美術(shù)論文 戲劇論文 導(dǎo)演論文 表演論文 音樂論文 哲學(xué)論文 歷史論文 社會學(xué)論文 邏輯學(xué)論文 美學(xué)論文 倫理學(xué)論文 心理學(xué)論文 文學(xué)論文 廣告論文 公共關(guān)系論文 新聞?wù)撐?/a> 外文學(xué)論文

期刊百科問答
- 攝影藝術(shù)領(lǐng)域AHCI期刊推薦《Photog
- Nature旗下多學(xué)科子刊Nature Commu
- 中小學(xué)教師值得了解,這些教育學(xué)期
- 2025年寫管理學(xué)論文可以用的19個選
- 測繪領(lǐng)域科技核心期刊選擇 輕松拿捏
- 及時開論文檢索證明很重要
- 中國水產(chǎn)科學(xué)期刊是核心期刊嗎
- 國際出書需要了解的問題解答
- 合著出書能否評職稱?
- 電信學(xué)有哪些可投稿的SCI期刊,值得
- 通信工程行業(yè)論文選題
- SCIE、ESCI、SSCI和AHCI期刊目錄已
- 評職稱發(fā)論文好還是出書好
- 復(fù)印報刊資料重要轉(zhuǎn)載來源期刊(20
- 英文期刊審稿常見的論文狀態(tài)及其具